台北市鐘錶眼鏡業職業工會故事(上)
- 發布科室:勞動教育文化科
前言 台北市鐘錶眼鏡業職業工會(以下簡稱鐘錶工會)成立於1958年12月24日,初成立時定名為「台北市鐘錶修理業職業工會」,是全臺第一個鐘錶相關產業的工會組織,至今已逾60年歷史。隨著產業從草創、巔峰、沒落到再起,工會發展與臺灣社會從農業轉型為工業的進程息息相關,並見證鐘錶、眼鏡等產業的變遷與演進。 隨時代推演,工會服務內容也從單純的勞健保,轉變為技藝傳承與培育人才的溫床,工會裡身懷絕技的修錶師傅全力推動技職訓練,期盼在技職體系尚未開辦鐘錶專科前,能有完整的教材保存,莫使技師引以為傲的指尖技藝失傳。 第1章 第2章福州師、日本師,共創繁榮的高級產業鏈
無論是眼鏡還是鐘錶,在以農業社會為主的臺灣,這些精細產品都屬於奢侈品。除了從日本時代,有零星留日或師承日人的鐘錶師傅戰後在臺紮根以外,臺灣的鐘錶與眼鏡正式成為產業,故事得從國民政府遷臺開始說起。
戰後國民政府來臺,同時帶入豐富多元的百工樣貌,由於渡海跋涉,不方便搬遷大型家當,因此謀生工具輕巧的鐘錶師傅,便帶著一身功夫和幾支手錶隨船來臺營生,他們發現這行業在臺灣還有許多發展空間,回頭再拉著親友同鄉一同渡海,大家一起來到陌生的土地找機會。
於是渡海來臺的「福州師」與留日返台的「日本師」遂形成鐘錶業的兩大體系,也為臺灣正式開啟延續百年的高級產業鏈。
由農轉工的時代背景
由於臺灣早期為農業社會,除了臺北、彰化鹿港、臺南府城三大都會,大多數居民都是捲起袖子下田工作,「甭說眼鏡或手錶,那個年代連家裡的鐘都是奢侈品!」台北市鐘錶眼鏡業職業工會理事長張重光說。
在手上掛著手錶就等同有錢人的時代背景下,臺北市相對其他縣市發展更快速,隨著學校與公司行號增加,百工產業興起,使市民對於鐘錶眼鏡的需求大增。
張重光說,早年臺灣還沒有自行製作的手錶,市面上流通的多是福州師傅帶進來的手錶,隨著臺灣從農業社會轉為工業社會,手錶的需求漸漸增加,市面上也開始流通各種愈來愈精緻、複雜的機械錶。當時有些維修問題,連福州師傅也不懂得如何排解,大家只得拆開錶面慢慢摸索,從一次次經驗中逐漸累積一套修理心法。
而鐘錶當時在臺北仍屬於經營門檻較高的行業,不只進貨成本高,開業的店租也貴,為了降低營運壓力,鐘錶店大多採複合式經營,最容易和鐘錶開在一處的,就屬於眼鏡業、銀樓業。
「早年流行的眼鏡都是圓形鏡框,是由福州師傅拿著玻璃和鐵棒,在砂輪機上親手磨出來的。」張重光說,鐘錶師傅所需的零件十分細小,螺絲起子等工具,恰好與配鏡所需的器材相同,因此早年鐘錶師傅大多兼作配鏡,兩大高價位產業最初始就採複合式經營。![]()
▲過去佩掛鐘錶是有錢人的象徵,這些流傳至今的名錶,在老師傅細心保養下已轉動數十年。(照片提供/邱秉儀)
百位成員草創起會
「那些前輩真的很努力,但回顧最開始,沒有個團隊,大家就像一盤散沙。」張重光說,由於當時沒有全權統籌事務的組織,導致修錶時沒有公定價格,各自營作業者總是隨意開價,日子久了,業界間惡性挖角、削價競爭的事蹟時有所聞。
為了解決市場上價格凌亂導致的產業亂像,又要使產業健康發展,1958年初,工會創始人鄧振斌、楊映雲、陳金樂等人,初期決定成立類似工會的民間團體,彼此討論公定價格,同時聯絡同鄉感情。
幾個月後,看見其他產業在政府輔導下成立工會,鄧振斌等人考量工會若要長久維持下去,必須有政府出面協助,他們決定從民間組織改組成正式的工會團體,並配合政令推動,額外承接勞保業務。
當時全臺北市僅約有兩百多家鐘錶眼鏡店,鄧振斌等人開始逐一奔走,最後找到近百位志同道合的成員,組織全臺第一家鐘錶眼鏡業的工會,並定調為「鐘錶修理業」,終於在1958年12月24日,成立「台北市鐘錶修理業職業工會」,他們是第一個,也是全臺唯一鐘錶眼鏡業的工會,當時臺北縣(現為新北市)許多相關從業人員,也都跨區到臺北市加入工會。
「因為鄧振斌為了工會忙到一頭白髮,我們以前都叫他『白毛仔』,草創時期真的苦,他常帶著幾個同業,包括我爸爸(林榮俤),滿街上到處去跑,一家一家募款。」常務監事林政良說,早期工會成立需要費用承租會所、聘請會務人員,但當時鐘錶業營運成本高,業者幾乎都把所有存款投入店面營運,在早期生意尚未起色的日子裡,「其實說穿了,表面光鮮亮麗,關起門來的日子都十分艱苦。」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鄧振斌為了籌募費用,吃足苦頭。無論晴天雨天,他們只得跨上腳踏車一跑再跑,遊說新店家加入,也得向會員募資收取會費。
所有工作裡,最辛苦的便是每個月收會費的時候,資深理事回憶:「以前工會根本沒甚麼福利可言,大家聽到加入工會還要樂捐,躲都來不及了!」鄧振斌往往一天跑了好幾間錶店,老闆都躲起來或閉門不見,為了收取會費,他只能耐著性子多跑個兩、三趟,最後老闆們礙於情面不好意思拒絕,只能勉強掏出錢來。![]()
▲台北市鐘錶修理業職業工會於1958年成立,初期鐘錶業因為入門門檻高,又被譽為穿西裝的行業。(圖片提供/台北市鐘錶眼鏡業職業工會)
走過倒會危機
工會成立初期,會員人數僅百餘人,加上無固定會所,只能四處承租辦公室,由於有不少會員日子過得艱辛,無力繳交勞保費,工會營運之初只能說是篳路藍縷,甚至窮到連總幹事的薪水都發不出來。長期入不敷出,導致財務無法周轉,挖東牆補西牆的結果,使工會內部財務形成一大筆濫帳,期間勞保局還以積欠勞保費為由,對工會處以停保處分。
這樣的結果看在當時已轉任常務理事的創會長鄧振斌眼裡,著實心痛又難過,他與一幫志同道合之士持續為會務奔走,甚至帶著工會全體理監事向臺北市社會局陳情,並轉請勞保局准予復保,最後雖然保住工會,但也在當時已風雨飄搖的財務狀況中,累積一筆高達3萬6千元的罰款。
在1960到1970年代,當時清洗一支手錶,僅能賺取20元工資,量身訂做一套西裝,才約1,000元上下,更不用說一般公務員每月薪水僅僅7、8百元。面對如此高額的罰款,工會與政府協商分期10年,以月繳300元的方式,艱辛且刻苦地走過工會重生之路。
由於每個月還款額度高昂,工會無力再承租會所,1973年,時任常務理事的劉公傑將住家客廳捐作工會辦公室,並自掏腰包支付水電費等雜支,長達7年期間不對工會收取一分一毫,使工會得以在辛苦的日子裡,一面還款一面存錢,逐漸奠定購買會所的財務基礎。
如此寄人籬下的日子轉眼過了7年,工會的財務危機終於減輕,大家開始思考購買會所事宜,於是全體理監事和會員開始小額捐款,透過不斷募捐,集腋成裘,終於購買屬於全體會員的會所。
1980年3月,中華路二段一處五樓舊公寓裡,僅27坪的會所,成為工會打拚22年後的第一個家。![]()
▲綽號「白毛仔」的鄧振斌,是工會創始人,也是促使工會發展的靈魂人物。鐘錶工會辦公室高高掛著創會長鄧振斌的照片,與一只日本麗聲品牌早期生產的電波鐘。(照片提供/邱秉儀)開啟專業勞工時代,鐘錶與眼鏡複合經營
1970年代以後,臺灣轉型為工業社會,百姓對高價鐘錶與眼鏡的需求逐漸增加,時鐘成為家庭依賴的報時工具,名錶更是身分地位的象徵,在臺北市蓬勃發展的鐘錶業,是人人稱羨的行業,也開啟有尊嚴、有水準的專業勞工時代。
改名鐘錶眼鏡業
當時因為高價鐘錶是婚慶儀俗中不可或缺的禮品,因此常見鐘錶店與銀樓一起經營,後來隨著讀書人口增加,配鏡需求也大增,也有愈來愈多配鏡行與鐘錶開在一處,於是在工會裡,眼鏡業的同仁數量日益增加。
1974年,工會應眼鏡業同仁游曉洋的申請,將名稱內的「鐘錶修理業」變更為「鐘錶眼鏡業」,把原先只是附屬的眼鏡業納入工會組織,此舉不只領先全臺,在普遍風氣傳統的工會內部更是一大進步變革,鐘錶眼鏡工會尊重各行各業的態度,博得大家的敬重,也使會員數穩健成長。
「大約到1960年代以後,鐘錶和眼鏡慢慢分家,漸漸形成獨立的眼鏡業,到1970年代成為高峰,因為當年的學徒逐漸成為師傅了。」張重光說,相較鐘錶的零件動輒數百種,眼鏡的結構單純許多,早年想學習鐘錶的學徒,許多會在閒暇時間兼著學磨鏡片及配鏡技術。
常務理事王景晃精通鐘錶與配鏡,他回憶起早期,配鏡時都是採用玻璃鏡片,客戶只要挑選好鏡框後,由師傅在玻璃鏡片上用簽字筆描出鏡框輪廓,接著使用兩根鐵條夾住玻璃鏡片,再用鐵條切出雛形後、再用砂石輪慢慢地磨,把玻璃磨到吻合鏡框大小,作業時,玻璃碎屑往往落在木箱內,作業時稍有不慎還可能受傷,「所以要看一個師傅功夫到不到家,看他的鐵條就知道,切到最後連鐵條都磨出凹痕,這才是真功夫!」他驕傲地說。
在那個年代,社會風氣講求「萬貫家財不如一技在身」,拜師學藝是社會上常有的事,當時也有許多外縣市的學徒來到臺北,學習最尖端的鐘錶維修技術,然後回到家鄉開枝散葉。
其中有些學徒在學習過程中找到明確的興趣,希望從事單純的眼鏡業,他們便成為如今超過一甲子歲月的老字號,後來眼鏡市場隨著國民教育普及而增加,因此學校開始出現視光學系,許多學生畢業後便投入眼鏡行業,眼鏡專門店在臺北市如雨後春筍般崛起,連帶使得工會人數不斷攀升,在1991年左右到達最高峰,工會人數從最初數百人一路成長至最高達八千多人。![]()
▲資深鐘錶維修師傅王景晃,多年來都是掛著放大鏡,細細拆解百年前的古董鐘錶。(照片提供/邱秉儀)
辛苦的師徒制
由於鐘錶或眼鏡行業,在更早期都沒有相關學習管道,最常見的入門方式就是師徒制,現任王常務理事、李常務理事也是拜師學藝出身。「我的師傅跟我說,3年讓我入門,真功夫要自己磨練,熟能生巧,舉一反三。」他和坊間大多數學徒一樣,經過三年四個月刻苦的拜師過程,最後再用一輩子的時間不斷自我精進。
說起當學徒的那段日子,他以走迷宮為例,打開機械錶的錶面,面對動輒數百個零件的機械錶,學徒就像是走入看不見盡頭的森林,師傅頂多告訴他們一條路,讓他們從起點走到終點,雖然是在森林裡自已摸索,但還可以摸索出很多條抵達終點的路徑。
因此真正的老師傅都是經無數的手錶維修經驗中千錘百鍊,進而磨鍊出精湛的技藝與眼光,「真正的老師傅,只要看到一支錶,光看外觀就知道裡面的構造,聽著客戶說有那些問題,還不用拆開,就知道該怎麼修了。」
有趣的是,雖然都是師徒制,但拜入「日本師」或「福州師」名下,所學可大不同。
會有這般差異,也是和彼時的時代背景有關。以前在鐘錶維修產業上,分成福州師傅和日本師傅兩大派系,雖然大家都會把錶修好,可是各自有不同的學習技能和維修手法。因此發展到1970年時,規模較大的鐘錶店甚至會聘請日本與福州兩位師傅,遇到客人上門維修手錶時,還會先問對方是哪裡人?再決定由福州師傅還是日本師傅去修理、更換零件。
兩大派系主要差別在於根據的輔助工具不同,技巧也會有所不同,而零件的名稱也不一樣。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要推出系統化的教學沒那麼簡單,若是有心入門學習鐘錶維修者,都還是得經過拜師學藝,然後不斷自我精進這個過程。
常言道「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師傅坦言,派系與技術這種東西,每個師傅一定都認為自己的最好,所以無論是福州師傅或日本師傅,兩派平日素來鮮少交流,唯有來到工會則海納百川,他笑說,「不同門派的師傅,只要進到工會會所都平起平坐。」
隨著戰後經濟起飛,鐘錶與眼鏡產業一窩蜂成長,加上有勞保單可以補助看診費用,1980年到1990年,加入工會的人數直線上升,也促使工會在勞健保業務之餘,推出更多的會員福利。
因此在1991年,除了提供原有的勞工培訓課程外,任內還積極推動會務並加強會員福利,例如規劃會員子女獎學金、會員互助金,大幅舉辦勞工教育和自強活動等,使工會與會員關係更緊密。
正當大家都為工會會務運作蒸蒸日上而感到欣喜時,一個隱憂出現了。1995年全民健保開辦,短短一年內流失近半會員,加上後來國民年金開辦後,再度衝擊傳統工會的運作功能,如今只剩不到4,000人留在工會,也使工會面臨到轉型的契機。
而早期鐘錶眼鏡業職業工會的會員組成是鐘錶業人數遠大於眼鏡業人數,近幾年因為各自專業化,眼鏡業有專業的產學一條龍,而鐘錶業則在時代趨勢下愈來愈少,日漸沒落,因此會員人數在前幾年逐漸翻轉,目前反而由眼鏡業成員成為工會主力。![]()
▲鐘錶工會同時也是專業工會,目前由工會資深李常務理事擔任講師,肩負世代傳承的重責大任。(圖片提供/台北市鐘錶眼鏡業職業工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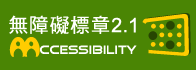
![我的E政府 [另開新視窗]](/images/egov.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