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企業工會故事
- 發布科室:勞動教育文化科
前言 國家兩廳院指的是國家戲劇院和國家音樂廳(以下簡稱兩廳院),於1987年興建落成啟用,1992年由教育部成立「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負責維運管理。數年後,由於「行政法人」制度興起,[1]為使兩廳院之營運更專業自主有彈性,在時任文化中心主任朱宗慶推動下,於2004年由一個政府機關改制為公法人機構,並於2014年移撥由文化部監督之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管理。 兩廳院是我國第一個行政法人機構,改制初衷係期許為臺灣的藝文展演注入活力與創新,殊不知接連組織調整帶來的人事與財務制度變革,卻引發了一連串勞動條件與福利權益之爭,使得兩廳院員工不得不挺身維護自身勞動權益。 第一章 2004年改制行政法人,勞資關係嚴重傾斜 改制前,兩廳院員工約有4分之1屬公務人員,且多是管理職,或分屬於財務、行政、人事等部門,另有4分之3成員為約聘僱人員,[2]其薪點與職務亦有一套法制化的管理機制,相關福利也比照公務人員,然改制後,所有約聘僱人員一夕間轉為勞工身分,[3]而且只能被動接受。 舊瓶裝新酒,矛盾衝突立現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企業工會(以下簡稱兩廳院工會)及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企業工會(以下簡稱國表藝工會)創會理事長淡成偉直言,由於身處主管職的仍是那些公務員,仍維持公務體系的管理思維,而另一邊則是多數必須適應勞工身分的員工,雙方都需要時間轉換心態,但組織運作不能停,於是隨兩廳院齒輪繼續轉動,「資方」與「勞方」的矛盾與衝突立即浮現,組織內部的權力關係也明顯地擠壓與傾斜,員工的勞動條件徹底地由上面說了算,「改制後,主管的權力可以直接影響我們的年終獎金、績效獎金,甚至未來加薪……」淡成偉表示。 行政法人成立之目的與任務之一,即是強化成本效益與績效。因此改制後,兩廳院上層便喊出「5個人的工作,3個人來做,領4個人的錢」,祭出控管人事成本的第一步。而接下來的10年,兩廳院的勞工福利不斷縮減,包括將國民旅遊卡(強制休假旅遊補助)改為休閒旅遊補助1萬元、縮減午休及彈性打卡時間、取消交通津貼、未履行三節獎金承諾、大幅刪減結婚和喪葬津貼等,「是拿員工的權利去幫兩廳院省錢」一名工會幹部這麼說。 這類犧牲員工權益的作法,在員工的勞工退休新舊制選擇上更是經典。[4] 一名工會幹部忿忿不平地表示,由於勞退新制與舊制的相關細節,時任主管並未多加說明,以致許多員工在未釐清自己權益的情況下,聽從上級的說法,簽署選擇新制同意書。若主管說明清楚,當時有多位年資近20年的員工,一定會選擇舊制,因為結算下來,新制下的退休金少了近百萬。[5] 現任兩廳院企業工會理事長李惟綱表示「那時候組織的思維就是,開源很難,節流比較快」,因此,兩廳院的管理策略在掌控營運成本與取捨勞動條件之間做出的抉擇,成為埋下觸發勞資衝突的導火線。 ▲改制後的兩廳院,勞工福利縮減情形表 做到流汗 嫌到流涎 早在改制的前一年,時任中心主任的朱宗慶便會定期發信給兩廳院員工,以宣揚改制「行政法人」的好處,也曾在專欄裡寫道:「行政法人的性質是一個專業、有競爭力、有企圖心、有清楚願景的單位。它的作法是由政府給予一定的保障,管得少、給得多,但受到公開透明的強力公法監督。」 然而「管得少、給得多」這根誘人的蘿蔔,其實是個再怎麼努力也吃不到的幌子。上層一再強調「只要做出成績,就有機會加薪」,員工把話都聽進去了,主動積極地攬起工作做,但卻沒有得到任何獎勵,「我就是被這樣子啊,我問主管加薪,他說有報上去是上面不准。」一名工會幹部無奈表示,主管將無法加薪的責任都往上層推,員工們雖憤懣不平,卻也無計可施。 當初,為了做出成績,2006年第一場大型節目《歌劇魅影》來臺演出,兩廳院員工一連拚了3個月都沒休息;隔年法國陽光劇團《浮生若夢》的演出,亦是如此。「雖然,獎勵、加薪遲遲沒有下文,但真正的引爆點是『TIFA旗艦計畫』」淡成偉說。2009年開始的旗艦計畫,囊括了《歐蘭朵》、《鄭和1433》、《茶花女》等一連3年的節目,員工們都超時工作,「甚至24小時沒有回家,過年期間也一樣」。 此外,為求提升服務表演團體的品質,上層提出「任務編組」,針對特定演出節目安排特定人力以協助表演團體順利完成演出。這項制度的立意良善,「透過我們組成的小組,全心投入主辦節目的演出任務,包括事前技術資料研究、與演出團體溝通討論等等」淡成偉說明,這有利於國外團體更快掌握場館硬體、提升技術效率。 但以「任務」為導向的工作責任,讓原本就常態加班的演出技術部門工作負擔日益加重,超時工作的情況也更為嚴重。為了「做出成績」,員工不像以往只在旁協助表演團體,改而紛紛跳下去親自操作,以確保演出順利,「就是像工頭啦」淡成偉說。 但這樣積極的態度卻弄巧成拙,「攬起工作做」卻被演出單位認為是撈過界,「我記得那時好像一直在搶人家工作」淡成偉回憶起來也這麼說道。 然而,面對此景,兩廳院主管不是趕快出面與演出單位溝通協調,而是反過來責備員工,「我們這麼努力工作,被外面人嫌,還要被主管罵,好像大家都可以罵你。」從那之後,淡成偉便選擇不再悶不吭聲、埋頭苦幹,他看出這是一個困境,他說,主管明明知道會發生這樣的問題,卻沒有想辦法解決,反而對員工們破口大罵,因此會和主管在會議上爭執,並意識到上層如此的管理模式,只會讓基層員工更辛苦,需要有人站出來改變這樣的處境。 另一引爆點則是績效獎金,淡成偉批評此一制度「走樣」,在改制初期,獎金計算以級等分別,大家所領金額相差不大,而2009年後,每個員工都更積極努力工作,但績效級距卻反而越差越大,「有人只領幾千塊,有人可能領十幾萬,但其實做的事大同小異」,因而引爆存放於員工心中已久的怒火。 ▲兩廳院演出技術部長期受加班、過長工時所苦,這些員工也是最早簽署工會發起人。(圖片提供/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企業工會) 第二章 2014年國表藝掛牌前的人力盤點,促使工會成立 一開始淡成偉只知道應該要想辦法解決勞動問題,但卻壓根不清楚「勞動三權」到底是什麼,直到在好友的牽線下,認識台北捷運工會理事長王裕文。 遇上捷運工會理事長 才萌生創立工會念頭 2009年,淡成偉第一次與時任捷運工會理事長王裕文見面,向他說明兩廳院員工的狀況,王裕文聽聞後隨即建議成立工會。當時正值《工會法》即將修法,王裕文除向淡成偉一一解釋什麼是工會、如何成立等重要資訊之外,也指點淡成偉俟修法後,可成立企業工會。[6] 在與王裕文會面之後,淡成偉也勤奮地做功課,自行搜尋、查看相關資料,才知道爭取勞動權益可以不用孤軍奮戰,淡成偉說「在這個之前,完全不曉得原來臺灣是有工運這件事情,也慢慢知道工會要怎麼運作,政府也有相關的措施、法令去保障工會的組成,而且官方也會輔導你籌組工會,以前都不知道什麼勞動局,接觸之後,才知道政府有這一方面的法令、機構可以幫忙。」 後來,淡成偉與王裕文還見了幾次面,並把握機會向王裕文請教,例如捷運工會內部事務、如何爭取到權益,甚至是有關於工運界現況等問題,而王裕文也將一身經驗傾囊相授。在累積一定的相關知識及熟悉背景後,淡成偉決定朝成立工會的目標努力,並照著王裕文所叮囑的「不要聲張」,私底下一個個慢慢尋覓30位工會連署發起人的合適人選。 從身邊信任的人低調號召 「我連我們算不算是勞工、適不適用勞基法都不知道」淡成偉雖決心要找到30位發起人連署成立工會,但卻連改制後的法定身分都不確定,資方從未明確表明全體員工適用《勞基法》。因此,淡成偉第一件事就是去信問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臺北市政府勞工局(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前身)確認身分認定問題,收到回覆內容為:「依據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屬於公立教育訓練服務業中之公立社會教育事業,該單位之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不包括依聘用條例、行政院暨所屬行政機關約聘人員僱用辦法進用之人員等),自民國97年1月1日起適用勞動基準法。」 ▲工會成立之後,第1屆理事長淡成偉也經常參與聲援友會的活動。(圖片提供/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企業工會) 在確認員工適用《勞基法》後,淡成偉便從身邊信任的好朋友開始詢問,「至少這樣,對方若不願意簽署也不會出賣我」,只是沒想到所找的同事竟全都簽下連署。淡成偉自豪自己看人的眼光並得意地表示「有幾個關係好的同事,雖然大家會一起吃飯、喝酒,但當我在闡述一些『勞資雙方』的問題時,若發現他對勞權並不是很友善,我就不會詢問。」 從2009年開始號召,淡成偉向每個受徵召的同事解釋什麼是工會、工會能為員工做些什麼……,歷經3、4年時間的檯面下運作,連署發起人終於達近20位,而這些人全都是整個組織中唯一受苦於「工時銀行」的演出技術部門的員工,[7]「因為只有我們部門,最有被迫害的感受。」同屬技術部門、負責燈光的淡成偉說。 「改制前,每月加班時間就已經是7、80至100個小時了」一位技術部員工說道,甚至出現一天工作20個小時的狀況。由於演出技術部門需要配合演出團體,早就是兩廳院中加班最為嚴重的部門,只是,當時至少每天上班時間固定,分成早上9點、下午1點兩班,且是全額給加班費。 兩廳院改制之後,工時計算方式改為以1個月的總工時作為單位,超過總工時的時數,才能算加班費,而且上班時間也不再固定,「今天有可能上2個小時,明天上10個小時,後天上12個小時,都是前一天才告知你」、「你某天雖然做了15個小時,但沒有加班費,因為昨天時數不夠。」一名工會幹部回想當時惡劣的勞動環境。現任兩廳院企業工會理事長李惟綱更曾在一檔節目表演結束後,接續幫下一檔演出團體搶時間搭景準備,導致一連工作25個小時的情況。 兩廳院人力盤點 助達發起人門檻 2014年,「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以下簡稱國表藝)正式掛牌成立,[8]意味著臺灣表演藝術邁入嶄新里程碑,而這對於兩廳院企業工會的成立,也是一關鍵時機。 為迎接國表藝掛牌,兩廳院於2013年進行全面性的人力盤點,資方說法是「將人力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但淡成偉表示,負責執行的1、2級主管實則針對某些員工,有些部門主管還專門找身障人士,進行強迫性每日約談,甚至要員工簽下優退、優離同意書。與其說是約談,其實更像找麻煩。 「這時候大家才驚覺,原來改制之後,工作權會受到影響。」雖然工會還未成立,但已經開始有其他部門員工主動找上淡成偉,希望幫忙解決問題,淡成偉當時滿腦子想的都只有「工會成立就什麼都解決了啦」,因此開始號召其他部門員工簽署發起人。 「但找別的部門的同事加入,就沒這麼順利了」淡成偉表示,畢竟比不上同部門的人來得熟悉,常遇到「找不對人」的窘境,像是之前曾被同仁在電話裡破口大罵「是要害我嗎?」,淡成偉只能回嗆「你不加入沒關係,但(成立工會)消息洩漏出去,我就知道是你做的。」 隨著國表藝成立,淡成偉找到37位發起人,除了演出技術部門員工,還有公共溝通、工務暨安全事務,以及行政管理等部門的同仁加入。 第三章 一步步將勞教帶進兩廳院,工會實質制衡資方 當時兩廳院現址登記著「國家交響樂團產業工會」,因此在組織工會上毫無經驗的淡成偉聯繫上其中一位團員朱偉誼老師,希望能向其請教成立工會的事宜,朱老師不但樂於分享經驗,也幫忙接洽上級工會「台北市產業總工會(以下簡稱產總)」,由產總秘書黃健泰接續協助淡成偉,在雙方積極商討之下,最終決定先成立「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企業工會(以下簡稱國表藝工會)」。 淡成偉解釋,由於國家交響樂團產業工會屬「廠場工會」,隸屬於國表藝[9]之下,登記廠場工會之上一層級、事業單位的「國表藝工會」,具有連結其餘兩館一團勞工的能力,可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企業工會終於在2014年10月23日成立。 在成立兩廳院工會前,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企業工會先於2014年10月23日成立。但不意外的,國表藝工會成立大會也是一波三折。原先計劃中午12點在兩廳院舉辦成立大會,卻有非會員的同事跑來詢問成立大會的時間、地點,在疑似走漏消息的情況下,只好急忙在11點半時,以成員間口耳相傳的方式,一個一個通知更換地點,最後改在中正紀念堂小森林、靠近公廁旁的位置,伴隨著從葉縫中灑下的陽光,工會成立大會終於順利召開。「有點像興中會一樣。」理事長笑著說道。 「我以為成立工會後,一切就結束,沒想到成立才是辛苦的開始。」淡成偉說,工會成立後,就像被貼標籤一樣,處處被針對,主管甚至在他工作時,衝上舞台當眾謾罵咆哮、刁難他的工作,「我身為理事長,請你們要尊重一點,我代表所有會員。」面對如此窘境,淡成偉不正面衝突且不卑不亢地回應,透過表明身分,一再強調與資方的同一高度,展現身為工會領導者的氣度,也站穩工會的立場和腳步。 為了讓工會幹部、會員感受到工會運作是玩真的,一開始,淡成偉就一個人跟著產總一起衝撞資方。他也坦言,從號召工會發起人至剛成立的那段期間,壓力最大,當時還常常抱著棉被哭,而壓力大部分來自於必須獨自衝鋒陷陣,卻又完全不能表現出害怕的樣子,「我當一個理事長,如果害怕,工會幹部就會跟著害怕,工會幹部一害怕,會員也會怕。」、「我只能不斷的往前衝,讓幹部看到這樣真的是可以做下去的。我要顧好這些人,不能讓他們有任何差錯。」雖然有所懼怕,但仍然一肩扛下推動工會前進的重責。 當時,資方完全不把工會放在眼裡,強行逕自舉辦勞資會議。對此,在產總指導下,淡成偉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請求協助,經向勞動局確認,資方舉辦勞資會議,須有工會推選之勞方代表參加,因此工會作出提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的決定。而此事件也成為資方態度轉變的關鍵,至少開始正視工會的存在。 從一開始便站在第一線協助國表藝工會成立、運作的產總秘書黃健泰表示,藝文業的特殊工作型態,加上兩廳院是從未有工會協議經驗的公務體系,勞資雙方對於勞動權益意識皆屬陌生,對於曾聽聞兩廳院主管抱怨《勞基法》限制藝文業的營運、發展,更直呼「都民國幾年了還在講這個!」但也因為知道整個組織的勞權意識仍未啟蒙,因此,黃健泰最初並不急著藉由勞動檢查的公權力,介入兩廳院的勞資糾紛,因為罰歸罰,最終還是要看勞資關係有無改善。因此,初期產總花了很多時間與工會幹部及會員討論,說明各種問題的解決策略及後續可能的影響,先讓工會了解與資方互動的「眉角」,並不時提供其他工會的經驗,或媒合與其他工會交流的方式,協助工會幹部提升協商能力。 兩廳院工會成立 當資方逐漸感受到工會日益壯大的力量時,開始有了危機意識,更有消息傳出資方計劃拉攏自己人欲成立兩廳院工會,以此與國表藝工會抗衡。[10]從當年號召到工會成立,一路走來,淡成偉早已培養出對資方任何風吹草動的敏感度。聽到消息隔天,淡成偉便拿著連署單,讓國表藝工會會員中屬兩廳院員工的會員再簽署一次,也找上當時兩廳院的工讀生,協助號召另外7名發起人,終達工會發起人門檻,並即刻向勞動局提出籌設申請。歷經千辛萬苦,「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企業工會」終於在2015年6月5日正式成立。 ▲聽聞資方有意拉攏員工籌組兩廳院工會,淡成偉隔日便號召發起人,不到一個月便達發起人門檻。(圖片提供/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企業工會) 從首役「爭取工時正常化」勞教會員 待一切準備就緒,淡成偉開始下一步─對會員實施勞動教育。為了把會員也帶上戰場,他選擇以實戰方式,帶領大家衝鋒陷陣,而第一戰,便是挑戰長年折磨演出技術部門員工的工時問題。 淡成偉召集所有會員,一一說明爭取「工時正常化」的各個面向,包括工時有哪幾種、如何爭取和運作等。而在開始進行討論、定案之前,淡成偉要求會員先簽連署書,「有點像畫押啦」,在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情勢下,必須先確定每位會員的改革意志。 為了訴求「工時正常化」,工會最後決定向資方提出兩班制的方案,分別為早班及晚班。早班為9點上班,可提前至凌晨5點加班,晚班則是下午1點上班,加班可至凌晨3點。工會幹部解釋,這是以演出技術部門一天內所能涵蓋的最多工作時間為考量所制定的方案。 然而起初,並非所有會員皆同意這方案,不少人因為加班費因此減少而有異議。對此,淡成偉和工會幹部一再曉以大義,「我們要的不只是工時,還希望在資方面前展現屬於我們的主導權、說話權,還要爭取勞資關係的對等」、「接下來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要爭取,不能為了眼前加班費,結果後面什麼都沒有了。」淡成偉秉持工會成立的初衷,不斷提點會員,而這次改革更關乎穩固工會與資方協商談判的權力與地位。 藝文業的工作模式特殊,一調整工時,可能連帶影響業務端、主管、場館單位、表演團體,甚至是承包單位,黃健泰對工會首役願意接下如此複雜的題目予以肯定,產總的角色除了提供醫護、工廠等相似工作型態的工會案例,給予建議外,更會模擬演練,扮演主管角色挑戰工會所討論出來的方案,以此逐步調整工時改革的成熟度,工會所提正常工時方案才迎來資方點頭,正式拍板定案。在2016年5月,兩廳院技術部開始實施兩班輪班制度,「執行之後,資方反而還比較省」黃健泰笑著說,不過,其他部門的工時也因此必須跟著變動,這加重主管階層的負擔,而讓勞資雙方的關係仍蒙著一層灰。 首役所爭取到的權益,雖然以演出技術部門為主,但實質意義更像一場訓練營,使得勞資雙方都熟悉組織運作中,存有「爭取勞權」的意識存在,而過程中所建立起的協商管道,也正是為爾後爭取更大權益及福利而鋪路。 淡成偉也說,為了不讓其他部門會員覺得,工會都只為「演出技術部門」發聲,所以之後向資方爭取的勞動權益,皆是涵蓋各個部門員工的有關權益,包括五一勞動節正常休假等休假權益改善、要求重視職業安全管理及績效獎金級距調整等等。而在過程中,產總皆扮演重要的角色,提供工會各種沙盤推演的步驟,並協助分析各方案背後的利弊及可能面臨的種種情境,就如同上戰場打仗時,有位足智多謀的軍師,替工會細細盤算如何打贏勝仗。 第四章 國表藝三館一團的合縱力量 兩廳院工會在一步步爭取內部員工權益的同時,淡成偉也沒放下對其他兩館一團實施勞動教育的想法。因此,藉著勞資會議的名義,以國表藝工會理事長身份南下到「臺中國家歌劇院」、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舉辦第1屆勞工代表選舉說明會。「我們暗藏很重大的動機,除了鼓勵同仁站出來選勞工代表,更是在教育同仁『勞動與勞權的概念」淡成偉笑說,國表藝工會存在的目的就是「刷存在感」。 ▲國表藝企業工會南下「臺中國家歌劇院」、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舉辦勞資會議說明會。(圖片提供/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企業工會) 在說明會上,淡成偉試著啟發他館員工們的勞權意識,強調參與勞資會議僅是第一步,並一一說明工會還能為勞工爭取的各項權益。經過說明會的加持,在第一次勞方代表選舉中,臺中、高雄的高投票率,也使淡成偉及其他工會幹部大為振奮。 「現在國表藝工會的戰略,就是佈點的方式,就像播種一樣,培養較有勞權意識的同仁成為種子,再讓這些種子將觀念逐步向外散佈出去。」但其實,早在淡成偉南下舉辦說明會之前,便有他館同仁向他請教成立工會一事。直到現在,仍保持聯絡、交換意見,不時詢問淡成偉勞權爭取相關問題。 截至今日,兩廳院工會在第2屆理事長李惟綱帶領下,持續在兩廳院內部爭取權益,而淡成偉則擔任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企業工會理事長,將工會影響力持續往外擴散。 第五章 未來課題與展望:經營路線出現分歧,期新血加入,傳承工會力量 「兩廳院勞資糾紛,員工依法請特休遭記曠職」2019年8月7日,有多家媒體報導這則新聞。這是兩廳院工會第一次將抗爭行動拉到館外,召開記者會,控訴資方刁難工會幹部,然此舉也讓勞資關係降到冰點。 與資方關係僵化 工會不洩氣 「走上街頭、對上媒體鏡頭是不得不的選擇」淡成偉說。休假是員工的權益,主管不准假,甚至直接記曠職扣薪,在調解未果下,工會才作出步出館外抗議的決定。 自此,資方態度變得強硬,關閉溝通的大門,「因為我們直接挑戰他的管理權。」李惟綱直接點出原因。 ▲2019年8月兩廳院工會第一次將抗爭行動拉到館外,舉辦記者會控訴資方。(圖片提供/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企業工會) 面對勞資雙方關係的寒冬,工會最憂心的是,員工的真實意見恐再遭漠視、埋沒。淡成偉舉例,以往若要實施變形工時(即彈性工時),資方會知會工會,由工會去詢問員工意願,並簽署同意書。如今,資方轉而直接找員工簽署同意書後,才行文告知,要求工會同意實施,工會成為被通知的角色。 此外,內部針對工會的負面輿論也隨之而起,更因此出現寒蟬效應,特別是剛進公司還不認識工會的新進員工,對工會避而遠之。李惟綱坦言,資方不溝通、內部員工不理解,是現階段兩廳院工會在爭取勞權上最大的困境。 「現在年輕人的想法是,來工作如果不合意就離職,我覺得這是不好的循環,因為就算到其他地方,也有可能遇到很糟的勞動條件,這是一種鴕鳥心態,無法根本解決問題。」李惟綱說。 同仁開始對工會產生質疑,也間接導致工會在第2屆勞方代表選舉中失利。淡成偉不諱言,企業工會的難處在於其幹部及會員皆為公司員工,而所要抗爭的資方,是每天都必須面對的直屬主管,這是非常有壓力的,多數同仁在尚未了解工會的存在價值時,看著工會遭到打壓,當然會選擇遠離,進而影響工會招募新血。 面對此況,工會並沒有放棄,仍努力找途徑與年輕人對話。淡成偉認為,年輕人表面上看來雖漠不關心,可是接觸後又覺得不太像,關鍵應是在於雙方的思考模式有極大差異。因此,提升年輕員工的勞動概念應是增進雙方交流及理解的第一步。 禁搭便車、與權益共享的路線之爭 工會現階段為努力打破與同仁之間的隔閡,同時又要低調行事,不與資方硬碰,因此主要宣傳方式為發放文宣。工會幹部們把握休息空檔,用一張張上頭印著工會聯絡方式的文宣,期藉由讓員工知道有與工會們聯絡的管道,慢慢撼動那道擋住勞權的高牆。 與此同時,工會也正為現階段困境找出路。過去,工會所爭取到的勞動權益,適用所有員工,這些權益都是工會幹部站在第一線承受各方壓力才打下的江山,然而有些員工卻將這一切視為理所當然,不免讓這些在前線衝鋒陷陣的工會幹部感到有種「為誰辛苦為誰忙」的灰心感。因此,內部也開始出現「禁搭便車」的聲浪,即工會所爭取到的權益,僅工會會員適用,「我們不用再幫那些未加入工會的同事爭取權益,等到他們遇到挫折或打壓,才會自己覺醒」有些工會幹部因此主張。在多數員工避而遠之、欠缺理解工會的情況之下,欲號召新血,必定需要等待時機,但李惟綱坦言這樣的時機,需要等且不好等,畢竟資方也在與工會的來回應對中習得經驗值,因此會避免讓這類(家醜外揚)的事情發生。 產總秘書黃健泰也認為,在尚未獲同仁認同及資方拒絕溝通的雙層擠壓困境中,目前工會並無實施禁搭便車的條件,重點仍需回歸到如何積極修補勞資關係上。 淡成偉則笑著說,自己本來是「理想派」,站在權益共享這一邊,認為成立工會,為大家爭取權益是應該的,加不加入工會倒是其次。不過,抗爭幾年下來,面對同仁未有感激之情,還種種針對、質疑,包括霸佔工會、私下拿好處等中傷傳言,淡成偉坦言,自己的理想正慢慢被磨損,而工會發展路線也確實需要調整。 現階段,工會路線該往哪條路走還未有定論,各有各的優劣,各有各的瓶頸與困境,因為,終究沒有一條完全合適的發展路線,只能不斷的修改調整。對此,淡成偉僅回說:「總會有辦法的。」也有不少工會幹部表示,對於組織現狀並不氣餒,認為工會還在運作的第一階段,與資方來回攻防、多條路線之爭,皆是必經過程,不過,一次次挫折底下,會員們磨練出來的堅毅逐日茁壯,這也成為工會日益穩固的基石。![]()
![]()
![]()
![]() ▲在國表藝企業工會成立大會上,產總理事長、公視及中華電信等友會都前來聲援。(圖片提供/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企業工會)
▲在國表藝企業工會成立大會上,產總理事長、公視及中華電信等友會都前來聲援。(圖片提供/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企業工會)![]()
![]()
![]()
![]()
![]()
▲兩廳院企業工會現階段宣傳方式以發放文宣為主。(圖片提供/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企業工會) ▲工會幹部們在工作休息空檔發放工會文宣。(圖片提供/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企業工會)
[8]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為文化部設立的行政法人機構,下轄三館一團,包括「國家兩廳院」、「臺中國家歌劇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以及附設團隊「國家交響樂團(NS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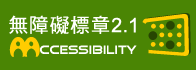
![我的E政府 [另開新視窗]](/images/egov.png)